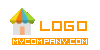第一次看完《霸王别姬》
很多人告诉我,《霸王别姬》,是经典中的经典。所以,把它下载下来,收藏在了《经典系列》中,却一直没有来得及看。或者,只是一次又一次地被打断。要么是最初开始唱戏的那段就已经看不下去,要么就是看到中途的时候突然有事离开,要么就是被两个小时五十一分吓唬了。如此,如此,也有四五次了吧。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心情,看完了《霸王别姬》。
从片头到片尾,一直怀着压抑的心情,而我却无力改变。
戏里戏外的人生,迷恋与背叛,冷漠与无情,纠结得我很心痛。
一个是为戏疯狂,成魔了,分不清戏里戏外;一个却把戏里人生和戏外人生分得如此清晰。
蝶衣已经出不来了,始终把自己当作虞姬。而师哥小楼,在戏台上是霸王,而戏外只是一个爱着菊仙的男人,过着琐碎的生活。
蝶衣是真正的那种可以称之为“疯子”的艺术家,像他这样的痴人,一旦走下舞台,走进现实的人群,注定是孤独的。
小楼是个把生活和梦想分得很清楚的人。少年时代义胆侠肠,但后来在凡俗生活中逐渐被社会和时间所消磨。就像他说的:“演戏得疯魔,没错。但如果活着也疯魔,咱在这凡人堆里怎么活?”
到底是戏如人生,还是人生入戏?
幼时的学艺经历,让蝶衣的性格发生了扭曲,开始是他对师哥小楼的依赖,而后逐渐转变了一种爱。他说,“说好是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行。”
作为师哥的小楼,是懂得蝶衣的那种微妙的心里的吧。可是,他没有蝶衣那么勇敢,他害怕世俗的鄙视。后来,他也有了自己喜欢的女子——菊仙。
从那天开始,一切都变了。他们再也不能回到从前。于是,他的信仰也随着破灭了。
他活得很真实,偏执,妒忌。
他憎恨小楼把菊仙娶回家,他恨师哥的心里有了别的人。
他们之间开始闹别扭,他们的关系出现了僵局。他们已渐行渐远。
世事变迁,清朝破败,日本侵华,新中国成立,文化大革命,更是摧残了他的一生。他的天真,他的诚实,都被利益的人民,不可琢磨的社会抹杀了。
可是,蝶衣只是一个戏痴而已。为何,要给他如此沉重的枷锁?
人一旦遭遇到了苦难,总是会变得很自私。
最重要的师哥背叛了他,“他为日本人唱戏,为国民党军官唱戏,为伪军伤兵唱戏,为太太小姐唱戏,他!他就是不为劳动人民唱戏!”一句句揭发,如刀子一样剜进他的心里。
天真的蝶衣,承受得起吗?
他的心被撕开了。一片,一片、、、、、、
痛,痛,痛。
于是,他也爆发了,撕心裂肺的咒骂:“我揭发姹紫嫣红,我揭发断壁残垣!”
看到这里,心被割得很疼。我数不清那些滚烫的晶莹,一滴,一滴,又一滴。 段小楼,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为何,为何要背叛自己最爱的女人,为何要背叛自己最亲的兄弟?
你和菊仙,昨天晚上才说着甜蜜的情话,说着你爱她的誓言,你忘记了吗?
你和蝶衣,你忘了你们的霸王别姬了吗?你忘了你们的深情绝唱了吗?你忘了你们的风华绝代了吗?
现实如此残酷,轻易地摧毁了蝶衣的梦。活着的蝶衣,只剩下一具躯壳。或许,愿意苟且的活着,只为了实现他心中的最后一个梦吧。
数年后,再相见。
师兄师弟二人终于重踏舞台再出演名流芳百世的霸王别姬,段小楼提不上气,程蝶衣再说思凡: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话语未落师哥便笑道又错了又错了,然而这次程蝶衣并没有错,他只是要回归自我。京戏创造了程蝶衣,如今他要回归到舞台上,于是虞姬拔剑而起,抽出袁四爷相赠的宝剑,于颈边喉上一抹,霸王惊愕。
这才是真正的《霸王别姬》,悲得如此凄美,凄美的如此惊艳,惊艳得如此华丽。
原来,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相关人物分析
程蝶衣活的最伤感,带着无尽幽雅的伤感。段小楼活的最可悲,带着满身无奈的可悲。菊仙活的最勇敢,带着坚贞顽强的勇敢。程蝶衣爱的最苦,段小楼爱的最累,菊仙爱的最真。
段小楼
张丰毅扮演的段小楼,揭露了背叛的人性。迷恋和背叛是人性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犹如冰与火的并存一样。少年时的段小楼--小石头为人爽朗、豁达,是科班的大师兄,在戏班的孩子中有威望有胆识,屡次为了救小豆子敢于受打挨骂。他刻苦用功,终成京城名角,因演霸王出名,身上也自然有股“英雄气”。救菊仙,娶菊仙,与日本人大打出手,倾家荡产救程蝶衣......因为这一身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豪情,程蝶衣景仰和迷恋他,菊仙喜爱和珍惜他。
他是个现实的人,在凡人堆里生活,他追求符合现实规则的男女之爱。段小楼是个角色意识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的男人,他有两个最执着的“女人”,分领了戏梦中和现实中的虞姬角色,而他在这两个选择间却暧昧难分、束手无策,周旋于两个爱人相互嫉妒和争斗之中,全无立场。
段小楼是一个性情中人,他对一切事物都很随性,对待任何人都傲慢。他更程菊二人矛盾的触发点。很多人说,段小楼不爱程蝶衣。我却不这样认为,他正是太爱程蝶衣,可是却无法面对同性这样的畸形恋才无奈的迎娶菊仙过门。相反,我却认为段小楼并不真的贪恋菊仙的美貌而草率的和她成亲。他们之间有的更是一种承诺和责任。而菊仙却史一个如此痴情的女子。
段小楼的性格是最可玩味的。一个极端矛盾的人,他为了救别人自己挨打,却在被打时口口声声的求饶。他突兀而梗直的惹恼日本人,却在文革期间出卖了他一生的挚爱!看似不可思议,却件件都在情理之中。
程蝶衣
程蝶衣自小是个固执的人,从他烧掉母亲给他的唯一的一件棉衣开始,他就表现出和一般孩子不同的性格。当他终于在师哥的强迫下背对了那句台词:“我本事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他的性别意识也由强迫性逐渐转化为自觉性。
随后,他爱上了“霸王”,他开始活在戏中,难以自拔。虞姬对霸王从一而终,霸王对虞姬情深意重。只有在戏里,只有英雄美人的故事里,程蝶衣才能找到自己的存在,才能找到一个与自己心灵相契的角色:虞姬。程蝶衣是倔强的,勇敢的,也是脆弱的:说他脆弱,是因为他爱上了自己的理想,不敢也不愿再回到这惨淡现世中来,直面自己真实的人生;说他倔强勇敢,是因为他偏偏又有这样的勇气固执地要这现实也照了戏来演下把去。 他就是一个“不疯魔不成活”的戏子。
程蝶衣坚执着的是艺术,只这两个字使他一生都宁愿孑然一身独立在时间的岸边,不管朝代更迭,不管世事纷扰,是最执著,也是最剥离的边缘性存在。这种存在只与心灵相关,这种存在拒绝和时间对话。他到最后被批斗时说了一句“你们都骗我”,他所说的“你们”是指所有的人,实际上是他自己在逃避现实,醒来为时已晚。在程蝶衣看来,没有了霸王,生和死即没有了区别,就象电影中的一句台词“是虞姬就终有一死”。霸王是现实的,虞姬是梦想的,所以当霸王别姬时,总是虞姬死在前面。
喜欢他,因为他的美丽,温柔,和不被理解的感情。蝶衣是幸福的,一如所有找到信仰和归宿的人一般幸福;蝶衣是美的,一如所有作为独立生命存在的性灵那般散着永难磨灭的美的光芒。陈凯歌说程蝶衣必须死,唯有死才能让他不朽,这句话早在千年前在虞姬身上就得到验证,她若不别霸王,世人不会记得她的坚贞和美丽。
菊仙
菊仙是全剧的灵魂女性,她美丽却不失大方,她爱的执着,爱的热烈,爱的深刻,爱的勇敢,泼辣又不失睿智,青楼的生活,窑姐的职业使她看尽世间丑态、世态炎凉,练就了她对待生活的一身铜皮铁骨。青楼悲惨生活带给她的不仅仅是痛苦,也使她在面对芸芸众生、时间百态时,拥有了一份从容镇定,甚至有一种驾驭生活的凌人的气势。蝶衣始终把菊仙当作“情敌”恨得咬牙切齿,而相比之下菊仙对蝶衣的感情十分复杂.
如果说程蝶衣是一个迷失在戏里和戏外、梦想和现实之间的虞姬,那么菊仙就是一个真正现世的女人,一个形而下意义上的虞姬。这个现世虞姬同样执著,同样"从一而终",只不过她所需要的仅仅是一个安稳的家,一个值得依靠的男人,一个最普通的女人所盼望得到的幸福。程和段都有性格上的缺陷,而身为女人的菊仙,给了他俩最无私的爱,她柔韧圆滑的处世风格僻护了两个最脆弱的男人。然而她是为爱而生的,她永远无法承受无爱的段小楼,所以她自己结束了生命。正如老鸨对菊仙说:“我告诉你,那窑姐永远是窑姐,你记住我这话,那就是你的命。”
霸王别姬——程蝶衣的变性心理分析
程蝶衣的悲剧正是始于童年的“创伤性情境”。影片中的程碟衣是一个身份认同的矛盾体,是天性与环境作用下对自己性别身份与形象的双重误认。母亲的妓女身份,注定了程碟衣小时候生活的环境——妓院里“男性形象”的缺失,而且母亲从小就把程碟衣当女孩养,这从幼儿期的女孩打扮可以看出,传达了其早期的身份与形象误认。自小豆子被母亲狠心切掉多余的一个手指,以鲜血淋漓的惨痛作为开场进入科班始,他的悲剧生涯便拉开了帷幕。正如影片中让他背弃自身性别,念“小尼姑我年芳二八,正青春被师父削去了头发;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一句话,硬是要从一开头就彻底地泯灭人的性别操守。
小豆子生活在一种单性环境中,而师兄对小豆子的关心与照顾,俨然成为小豆子心中缺席的“父亲形象”。当小石头用烟锅破小豆子的嘴之后,小豆子被迫念出《思凡》里的道白“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时,他对自我身份与形象的主观误认便开始了。在舞台上男扮女装的程碟衣,唱《霸王别姬》唱成了角儿,满堂响起喝彩声时,程碟衣体会到的已不是作为这个角色而获得的荣耀,从其表现看来,此时她而非他已经完全认同了“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的身份,并且充分享受着因“女娇娥”的优异表现而获得的众人的赞赏,这种满足令其陶醉不已。程蝶衣最爱演的虞姬死于刎颈,程蝶衣自称拿手好戏的杨贵妃死于上吊…… 程蝶衣的一生就这样重复着阉割的梦,从一开始的迫于接受,到后来的默认同化,代表着程蝶衣变性心理逐步坚定。
旧时权贵张公公、袁四爷的猥亵与狎玩,进一步造成了程碟衣对虞姬形象的“固置”。“尘世间,男子阳污,女子阴秽,独观世音集两者之精于一身,欢喜无量呵。”袁四爷这句话令程碟衣更加执迷于错乱的性别认同。自此,他有着一个男人的生理躯体,但生命本色却是虞姬这个唯美的剧情人物。他有男性的执著、沉默、内敛和坚忍,也有女性的敏感、温柔、聪明、细致、脆弱甚至有爱而生的嫉妒和自私;他对霸王开始了漫长一生的依赖与迷恋,戏里的异性恋演变成现实中的同性恋。
在影片结尾,当段小楼再念起“我本是男儿郎”,程蝶衣本能地接起了“又不是女娇娥”,这时的程蝶衣才猛然醒悟,生命中因为理想而选取、珍重的一切,须臾间都显示了令他无法忍受的沉重的本来面目,这个时候他才重新意识到自己的男性身份,然而此时已是“文革”后,在经历了一生迷恋之后,最终清醒也无力回天,对自身男性形象与身份的突然发现必然是对女性形象与身份漫长一生误认的否定,而对女性灵魂的维护只能是男性肉体的毁灭,程蝶衣只能以死告别这个世界,而其选择的方式仍是戏剧身份的虞姬拔剑自刎的情节,以实践从一而终的人生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