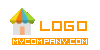喜欢中国古典诗词的外国朋友往往会有这样的疑问:“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这么钟情于妓女啊!几乎所有的诗词都是写给妓女的,难道她们是国家的精英,比广大的家庭妇女都美丽得多、可爱得多?”确实,中国古典诗词中充斥着关于文人与妓女的风流韵事,譬如50000首全唐诗中,专门写妓女的便有2000多首,而全宋词更可以作为青楼文学的代称,这种现象在世界范围内绝无仅有。在解释这一现象产生原因的时候,虽然我们可以“三从四德”的观念阻碍了家庭妇女的女性魅力,男人在家庭中得不到爱的温暖来搪塞,但这样的回答并没有涉及到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恐怕还是每个男人内心潜藏着“妓女情结”。
喜欢中国古典诗词的外国朋友往往会有这样的疑问:“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这么钟情于妓女啊!几乎所有的诗词都是写给妓女的,难道她们是国家的精英,比广大的家庭妇女都美丽得多、可爱得多?”确实,中国古典诗词中充斥着关于文人与妓女的风流韵事,譬如50000首全唐诗中,专门写妓女的便有2000多首,而全宋词更可以作为青楼文学的代称,这种现象在世界范围内绝无仅有。在解释这一现象产生原因的时候,虽然我们可以“三从四德”的观念阻碍了家庭妇女的女性魅力,男人在家庭中得不到爱的温暖来搪塞,但这样的回答并没有涉及到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恐怕还是每个男人内心潜藏着“妓女情结”。
“妓女情结”的产生和男人与生俱来的“花心”有紧密的联系。男人花心似乎是天生的,这或许与男女不同的身体构造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它与长期男权意识统治下男人对女人的控制与占有有关。这一男权意识,包涵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对女人占有的多寡,是衡量一个男人地位高低与成功与否的标志,故而古代的皇帝通常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但依然不满足,还巡幸民间,玩“游龙戏凤”的把戏,而普通人家,只要稍微有点财力的,都恨不得娶个三妻四妾,也好向外界炫耀。
另一个层次是男人对美的把玩与占有心态。这其实体现出男人将女人视为玩偶的潜意识,是将女人的地位降为与宠物古玩同列的心态。中国古代经常发生将女人赠人的故事,有意思的是,这样的故事不仅不会遭人指责,反倒成为文人名士间的风流雅事,大书特书。如南宋的范成大因词人姜夔写出一首好词,便将家中的歌妓小红双手赠送,从而在文坛留下“小红低唱我吹萧”的佳话。更有甚者,某位王公因为看中对方的一匹好马,心甘情愿将自己的爱妾拿去交换。这当然是极端的例子,“待遇”稍好一点的,便是将女人视作家中摆在最显眼处的一个花瓶,既可使满室争辉,也可向宾客炫耀,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
对美的欣赏与占有,属人之常情,我们不必大加挞伐,但问题是,你在欣赏和占有“美”的时候,是否采用了非正常的手段?如果将女人作为“美”的大家庭中的一员,你是否征求过当事者的意见,她是否愿意做你家中的一个“玩偶”呢?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可惜,大多数男人在“欣赏”和“占有”女人的时候,很少考虑到置身其中的女人的感受。因而这样的“欣赏”与“占有”,当然会遭到女人的强烈反对,并采取各种手段来抵抗之。如易卜生的戏剧《玩偶之家》中,作为贵妇的娜拉就是因为忍受不了丈夫将其视为玩偶的心态,愤而离家出走的。离家出走的滋味当然不好受,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不是流浪便是堕入风尘,但即使是这样,女人依旧乐此不彼,究其实,还是女人忍受不了男人那种自私的占有意识与玩弄心态。
其次,男人“妓女情结”的产生还与男人在家庭中很难获得真爱有关。古代社会,男人与女人的结合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种原则考虑的是门第、身份、地位,爱情是忽略不计的,更不用说男女之间的相互了解、性情相投了,因而大部分中国人的婚姻,是一种有性无爱的婚姻。中国的男人,尤其是那些自命不凡的才子,又迫切希望在现实生活中追求情与欲的合一,灵与肉的统一,故而那些多情而又放荡的青楼小姐成为他们感情与情趣的寄托。
最后,男人的“妓女情结”与男人成长过程中的性幻想与性渴望有关。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每个男人都有“恋母情结”,在成长的过程中,男人的恋母情结往往转换成对某个成熟女人的性幻想与性渴望。在潜意识中,男人对成熟女人存在着朦胧的性幻想与性渴望,这种幻想与渴望,承载着他们由少年成长为男子汉的憧憬与向往,即向往与这个成熟的女人完成人生的“每一次”。如《红楼梦》中,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与警幻仙子的妹妹发生性关系,其后,又与贴身丫环袭人“初试云雨情”,都表明贾宝玉潜意识里对梦中情人的追求与成长的渴望。
在对男人“妓女情结”产生的原因作一番简单的归纳后,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下这种“妓女情结”在现实生活中呈现的形态。
第一,男人的“妓女情结”表现为对“妻不如妓”观念的认同与实践。所谓“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妻、妾、妓在中国古代男人心目中的身份、地位迥然有异,在此无需详谈。关键的一点是,妻子很难像妓女一样拥有女性的魅力。中国的妻子很少拥有魅力,往往被称为“黄脸婆”,原因有二:一是“三从四德”的封建观念沉重地压在她们头上,为了不落下“勾引”丈夫的恶名,她们不敢轻易装饰;二是长期的家务操劳让她们的身体较早地“磨损”,皮肤粗糙,失去弹性,再加上眼角的鱼尾纹,因而比实际年龄显得要大些。试想,一个皮肤黝黄、眼神呆滞又生过小孩的女人,又如何靠她的性魅力来吸引男人呢?
第二,男人的“妓女情结”还表现为男人追求成功与自信的心理需要。男人内心其实充满着脆弱,因而他们需要别人的赞美与歌功颂德,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收获更多的信心。但现实生活中,妻子在男人面前举案齐眉,毕恭毕敬,又怎么会想到随时给男人“加油”呢?而作为朋友或同事,除非有求于你,一般也不可能对你溜须拍马。因而这样的角色只有由妓女承担,为了让男人爽快地掏腰包,这点“牺牲”还是值得的。
 在妓女面前,男人不仅地位高贵,受到她们的殷勤接待,而且,由于妓女的有意识地“吹捧”,男人追求成功的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自信心空前高涨。“驾临”青楼的男人,首先被妓女“官人”、“公子”的称呼熏得晕乎乎的,继而在酒精的刺激下,妓女们左一个“潘安之貌”,又一个“子建之才”,恍惚间让男人真的产生自己不可一世的幻觉,真如刘晨、阮肇在天台仙境逍遥,不知今昔何昔。
在妓女面前,男人不仅地位高贵,受到她们的殷勤接待,而且,由于妓女的有意识地“吹捧”,男人追求成功的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自信心空前高涨。“驾临”青楼的男人,首先被妓女“官人”、“公子”的称呼熏得晕乎乎的,继而在酒精的刺激下,妓女们左一个“潘安之貌”,又一个“子建之才”,恍惚间让男人真的产生自己不可一世的幻觉,真如刘晨、阮肇在天台仙境逍遥,不知今昔何昔。
第三,男人的“妓女情结”还表现在男人视女人为商品的心态。迈入青楼的男人,其实都具有清醒的意识,那就是,青楼的妓女是不会有真情的,嫖客与妓女之间,不是谈恋爱的情人关系,而纯粹是一种赤裸裸的金钱交易。明代《嫖经》曾经用两句话概括这种金钱关系:一句是“须是片时称子建,不可一日无邓通。”意思是说,一个没钱的嫖客,即便他有曹子建的“才高八斗”,依然会被扫地出门。另一句是“子弟钱如粪土,粉头情若鬼神。”潜台词是,到青楼潇洒的男人,即使花钱如粪土,但要想真正俘获妓女摇摆不定的“芳心”,只怕是“难于上青天”吧。既然妓女无情,嫖客也不需要承受过多的心理负担。正所谓“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一个投以金钱,一个报以美色,公平交易,皆大欢喜!不过,即便再赤裸裸的交易,总要打着爱情的幌子,毕竟,嫖客与妓女是走出了伊甸园的亚当夏娃,在进行交易时,他们必须扯上爱情的遮羞布。
第四,男人的“妓女情结”还反映在他们对妓女既爱又恨、欲拒还迎的复杂心态。一方面,男人将妓女想像成高贵的圣女、仙女,对其顶礼膜拜,极尽渲染之能事。如宋玉《高唐赋》中曾记载楚怀王梦游高唐,与“自荐枕席”的巫山神女共赴云雨之会,便是将妓女的神仙化。
又如张文成《游仙窟》中的崔十娘,其实便是作者“历访风流”时艳遇的妓女,但作者宁愿将她虚构成天上的仙女,居住在“人踪罕至,鸟路才通”的神仙窟,并赞美她是“博陵王之苗裔,清河公之旧族。容貌似舅,潘安仁之外甥;气调如兄,崔季珪之小妹。花容婀娜,天上无俦;玉体逶迤,人间少匹。辉辉面子,荏苒畏弹穿;细细腰支,参差疑勒断”。不仅地位高贵,出身于世家大族,而且气质超凡脱俗,崔十娘的“优秀”令世上最美的词汇都黯然失色。将青楼的狎妓经历包装成一次附庸风雅的浪漫之旅,这种想像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让男人的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从而验证了自己作为男性的尊严与能力。
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男人都对妓女心怀歧视,认为她们低贱下流,羞与为伍。男人对妓女的歧视,首先是因为感觉她们很脏,污染了社会环境。如北京的出租车司机,看到那些浓妆艳抹、身着妖冶的女子在街上揽客,往往会痛骂一声:“…鸡”。自然,这些女人没有招惹他们,但司机看她们就是不顺眼,故而需要用一句脏话来发泄心中的恶气。
其次,还在于男人始终将嫖娼的行为归咎于妓女的勾引,是她们让自己变成一个违背伦理道德的人。通常情况是,男人掏出钞票,女人脱衣上床,双方心照不宣地完成男女间最原始的“工作”,但一旦提起裤子,男女双方便形同陌路,就好像刚才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这让男人有一种受骗上当的感觉,再加上完事之后涌到脑海的羞耻感,令男人感到恶心与下贱,于是决定再也不干这样作贱自己的事了。然而,男人嫖娼如同吸毒一般,明知道它有害健康,有损名誉,但内心的欲望让他们又离不开妓女,因而会做出“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反常举动。
这一反常举动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晚清曾被称为“嫖界指南”的《九尾龟》,作者一开始便宣言,这本书本来就叫《嫖界醒世小说》,似乎在告诫、警醒读者嫖界是黑暗无耻的和利欲熏心,希望人们远离青楼妓院,但是,作者对章秋谷等嫖界圣手在花街柳巷的风流韵事却津津乐道,并将章秋谷的每次艳遇进行了细致入微的介绍,戒嫖与劝嫖同在,不仅起不到戒嫖的作用,反倒成为劝嫖的教科书与入门指南。
当然,男人“妓女情结”产生的原因还有很多,呈现形态也各式各样,但归根结底,它源自男人内心对占有女人的贪婪欲望,在这种欲望的驱动下,男人对妓女投入了较多的“热爱”与金钱,刺激了色情业的蓬勃发展,并使这一古老而极具生命力的职业,长盛不衰,绵绵不绝。